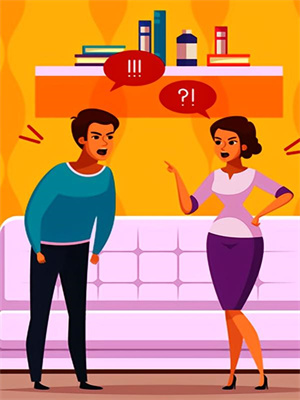简介
如果你喜欢都市日常类型的小说,那么《重回小时候之通天教主逗闷子》绝对值得一读。小说中精彩的情节、鲜活的角色以及深入人心的故事,都会让你沉浸其中,难以自拔。目前,这本小说已经连载,总字数已达129675字,喜欢阅读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重回小时候之通天教主逗闷子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年味儿,是被一阵紧过一阵的北风,从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一丝丝、一缕缕,硬生生刮进这方北方小城,刮进筒子楼那被煤烟熏得发黑的窗棂缝里的。先是空气里开始弥漫一种混合了硫磺、油炸物、蒸馍馍和尘土被冻得发脆的气味。接着,是楼道里、公用水池边,那些被生活磨得没了脾气的脸孔上,渐渐多了几分急迫的、躁动又带着麻木的期盼。再后来,是家家户户门上开始贴出红纸剪的窗花——多是“福”字,倒着贴,也有手巧的妇人,铰出“连年有鱼”或者牡丹花的轮廓,红彤彤的,衬着斑驳的木门,便透出几分与清苦日子不甚相称的、执拗的热闹来。
林桂兰也剪了窗花。是“喜鹊登梅”,纸是供销社处理的、颜色有些暗的劣质红纸,剪出来的花样也简单,没有邻居家那般繁复精细。但用稀薄的面糊贴在擦得格外透亮的玻璃窗上,那抹粗糙的红,便也硬生生在灰白的冬日天光里,燃起了一小簇暖。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林桂兰在厨房里忙活。今年实在拮据,买不起麦芽糖,她便用攒下的、舍不得吃的几粒冰糖,在铁勺子里用小火慢慢熬化了,拌上一点炒香碾碎的花生米,权当是“糖瓜”,粘粘的,甜得发齁。方唐蹲在灶台边,看着橘红色的火苗舔着乌黑的锅底,冰糖在热力下融化成金黄的糖稀,咕嘟咕嘟冒着细小的气泡,散发出诱人的焦甜香气。这香气混在弥漫的煤烟和水蒸气里,是记忆中过年才有的、奢侈的味道。
“妈,真甜。”方唐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将那一小勺珍贵的糖稀花生碎,抹在灶王爷那被烟熏火燎得面目模糊的神像嘴上,小声说。
“甜,就对了。甜了灶王爷的嘴,他上天说好话,明年咱家日子,就能甜一点。”林桂兰用指尖揩去勺沿最后一点糖稀,顺势抹在方唐微微张开的嘴唇上。冰凉的手指,温热的糖稀,奇异的触感。方唐伸出舌头舔了舔,甜腻腻的,带着一股焦香。他仰起脸,看着母亲。林桂兰的侧脸在灶膛跳跃的火光里,显得瘦削,颧骨突出,但眼睛里,映着那簇小小的火焰,亮得惊人。
灶王爷的嘴被糖封住了,想必是说不出坏话了。可日子,真能靠这点甜,就好起来吗?方唐不知道。但他知道,母亲在努力,用她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家,为即将到来的、注定清冷的年,增添一点仪式感,一点希望。这希望,如同窗上那粗糙的窗花,微弱,却真实。
年关,是穷人的“关”。这话,方唐以前听父母说过,此刻才真切地体会到了。要账的,躲债的,算计着一年到头、手里到底能落下几个子儿的,都在这时显出形来。林桂兰的眉头,在年关的迫近中,又锁紧了。方建国汇来的钱,一笔一笔,像涓涓细流,汇入这个干涸的家庭,解了燃眉之急,却也仅仅是“解渴”,远谈不上“丰沛”。房租要交,煤要买足,粮要备下,年节的吃食、哪怕是最简陋的,也得预备几样。还有,方唐的新年新衣,虽然用碎布拼了坎肩,但罩在外面的棉袄,袖口已经磨得发亮,肘部也薄了,总得想法子拾掇拾掇。
林桂兰开始更细致地盘算。她把家里所有的票证——粮票、布票、油票、副食票——都翻出来,摊在炕上,一张一张地看,用铅笔在旧账本背面画着只有她自己能懂的记号。哪样必须买,哪样可以省,哪样也许能找邻居挪借一点,哪样必须动用那所剩无几的现金。她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肃穆,像是在指挥一场兵力悬殊的战役。
方唐趴在她身边,看着她算。母亲的手指,因为长期浸泡在冷水里做活,指节粗大,皮肤皲裂,捏着那张薄薄的、印刷粗劣的布票,微微颤抖。那布票,是全家攒了许久才攒下的,本来计划给方建国做件新罩衫,现在,怕是要先紧着方唐了。
“妈,我的棉袄还能穿,补补就行。”方唐小声说。那件用碎布拼的坎肩,他已经很知足了。
林桂兰抬头看他一眼,没说话,只是伸手,将他搂进怀里,下巴轻轻抵着他的头顶。方唐能闻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混合了肥皂和淡淡油烟的气息,能感觉到她胸腔里传来的、压抑的叹息。
“没事,妈有法子。”她这样说,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韧劲。
她的“法子”,就是更拼命地接活。白天去街道糊纸盒的作坊,晚上回来,除了缝补自家和邻居的衣服,还从相熟的、在服装厂做临时工的女工那里,接了一些“私活”——缝纫机扎裤边,锁扣眼,钉商标。这些活计琐碎,工钱极低,按件计,常常忙活一晚上,也挣不到几毛钱。但林桂兰不嫌。她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蚁,在灯下,一针一线,一分一厘地,为这个家,衔回过冬的食粮。
方唐帮不上别的忙,只能更“懂事”。他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家务,扫地,抹桌子,生炉子,倒煤渣。炉火总是烧得不旺,他就一遍遍尝试,观察煤块的大小、摆放的疏密、通风口的开合,用他那日渐清晰的、能“看”到事物关键节点的“眼光”,去调整。他发现,当炉膛里煤块的摆放形成某种特定的、松散又有序的“结构”时,通风会更好,煤块燃烧更充分,火苗也更稳定。虽然只是微小的改善,但积少成多,能省下一点煤,也是好的。
他还“盯”上了家里那口旧铁锅。自从那次尝试“引导”后,他对这口锅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近乎“责任”的感觉。每次母亲用它炒菜,他都会下意识地关注。他不再轻易动用那种消耗巨大的“线条视野”,而是尝试用更温和、更持续的方式去“感受”它。他会趁着母亲做饭的间隙,用手轻轻抚摸锅壁,不是用皮肤去感受温度,而是用意念,去尝试“沟通”残片,去“触摸”那晚曾惊鸿一瞥的、锅体内部的“线条网络”。
起初,毫无反应。残片沉寂如故,铁锅也只是冰冷的铁锅。
但他不气馁。每天,在母亲炒菜前,他都会“例行公事”般,用手掌贴着锅底或锅壁,静立片刻,心神沉静,意念若有若无地缠绕过去,像是对一个沉默的朋友发出无声的问候。他不求看到那震撼的“线条世界”,只求能建立起一丝更稳定的、哪怕是极其微弱的“联系”。
奇迹没有发生。锅还是那口锅,炒菜时依旧受热不均,靠近炉心的地方容易糊,边缘则还是温吞。母亲依旧需要不停地颠勺、挪动锅的位置,才能勉强让菜受热均匀些。
但方唐没有放弃。这成了他的一种“日常修炼”,一种对耐心和心神的磨砺。他渐渐发现,当自己彻底放松,不刻意“看”,也不刻意“沟通”,只是将手掌贴在锅上,心神放空,仿佛与锅融为一体时,胸口残片会传来一种极其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的“脉动”。那不是发热,也不是震动,而是一种……“存在感”的增强。仿佛残片与他,与这口被他长久“注视”和“触摸”的铁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超越了物理接触的、极其淡薄的“联系”。
这“联系”虚无缥缈,毫无实际用处。既不能改善铁锅的导热,也不能让菜变得更美味。但方唐却从中体会到一种奇妙的、安定的感觉。仿佛在这冰冷而粗糙的现实中,他凭借这枚来自洪荒的残片,与一件最寻常不过的家什,有了一丝超越凡俗的、隐秘的共鸣。这共鸣微弱如风中之烛,却照亮了他内心深处某个孤独而奇异的角落。
年关一天天逼近。林桂兰终于咬牙,用那叠宝贵的布票,加上方建国最新汇来的一笔钱,扯回了几尺藏青色的、厚实的劳动布。这布不是做新棉袄的,是给方建国做罩衫的。她的理由很充分:“你爸在外头,见人,谈事,总要穿得体面点。旧衣服补了又补,不像样子。唐唐还小,穿旧点没事,过年妈给你把棉袄袖子接一截,领口换个新,一样精神。”
方唐没有争。他理解母亲的决定。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希望所在,他需要一件体面的衣服,撑起门面,也撑起信心。自己身上的破旧,反而成了父亲在外奋斗价值的无声注脚。
新布买回来,林桂兰没有立刻动剪。她将布在炕上铺开,用手掌一遍遍抚摸,感受着布料的厚度、纹理和挺括度。她的眼神专注而虔诚,像是在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然后,她拿出珍藏的、几乎没怎么用过的画粉,对着昏黄的灯光,开始打版、划线。
方唐就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母亲打版的手法,和他“看”到的父亲在信里描述的、王师傅那种精准流畅不同,更带着一种家常的、因地制宜的朴实。她会反复比量旧衣服的尺寸,会根据布幅的宽窄调整剪裁方案,会精心计算,如何在这有限的布料上,裁出最大的利用率,连边角料都要计划好用途——或许能做几个补丁,或许能拼一双鞋垫。
灯光将母亲俯身的身影投在墙壁上,放大,成了一个忙碌而专注的剪影。剪刀“咔嚓咔嚓”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带着一种斩断犹豫、迎向新岁的决绝。方唐看着那在母亲手中变得驯服的藏青色布料,看着那逐渐成形的、代表着父亲体面与尊严的罩衫轮廓,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是酸楚,是骄傲,是期盼,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名为“家”的实感。
这件衣服,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是母亲一针一线的祈愿,是父亲在远方咬牙坚持的见证,也是这个家在寒冬里,相互扶持、彼此取暖的凭证。它的每一寸布料,都浸透着生活的重量;它的每一道线迹,都缝进了对这个家庭未来的、最朴素的期许。
就在罩衫裁片即将完成,林桂兰拿起剪刀,准备剪下最后一片袖筒时,方唐胸口的玄黄鉴残片,忽然,毫无征兆地,轻轻“嗡”了一声。
不是声音,而是一种直接作用于感知的、极其细微的“震颤”。如同平静的湖面,被一粒几乎看不见的微尘击中,漾开一圈微弱到极致、却真实存在的涟漪。
方唐浑身一僵。
这震颤,与之前触发“线条视野”时的“温热感”不同,更微弱,更飘渺,带着一种奇异的……“共鸣”意味。仿佛残片本身,对眼前正在发生的、这充满“人”的意志与情感的劳作,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反应”。
他下意识地,将全部心神集中在胸口。
残片依旧温润,没有发热,没有异光。但那丝“震颤”的余韵,却清晰可辨。而且,这震颤并非指向某个具体物体(比如铁锅),也不是由他主动的意念沟通引发。它似乎……是对母亲此刻那种全神贯注、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手中衣料的状态,一种自发的、微弱的“共鸣”?
方唐屏住呼吸,目光紧紧追随着母亲的动作。林桂兰对此毫无所觉,她正凝神静气,锋利的剪刀刃口,稳稳地沿着划粉线行进,“嚓——”,一声轻响,布料顺从地分开,边缘光滑如镜。
就在剪刀裁开布料的刹那,方唐“感觉”到,胸口残片那微弱的“震颤”,似乎与剪刀行走的韵律、与布料被分开时纤维断裂的细微声响、甚至与母亲呼吸的节奏,产生了某种难以形容的、同步般的“和谐”。虽然只是一瞬,但那种感觉无比清晰。
不是力量,不是洞察。而是一种……“韵律”的契合?一种“状态”的呼应?
母亲此刻,心无旁骛,意念纯粹,所有的精神、经验、情感,都凝聚于指尖,倾注于这裁剪之中。她触摸着布料的“骨”(纹理),顺应着它的“性”,用剪刀这“笔”,书写着对远方亲人的牵挂与祝福。这种状态,这种将自身意志与手中之物、与所做之事高度统一、浑然忘我的“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某种……“道”?
裁衣有裁衣的“道”,洪荒有洪荒的“道”。这枚来自至高之处的玄黄鉴残片,莫非并非死物,而是在这最平凡的人间烟火、最质朴的匠心凝聚中,感应到了某种跨越了无尽时空与层次界限的、共通的“韵律”?
方唐被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震惊了。这太玄乎,太不可思议。但胸口残片那真实的、微弱的共鸣震颤,却又让他无法全然否定。
他怔怔地看着母亲剪下最后一片裁片,看着她长长舒了一口气,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眼中却带着完成一件重要事情后的、疲惫而满足的光彩。那件藏青色的、尚未缝合的罩衫裁片,平平整整地摊在炕上,像一片沉静的、等待被赋予生命的蓝色土地。
胸口残片的“震颤”早已平息,恢复成一贯的温润沉寂,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
但方唐知道,不是幻觉。
年关的“骨”,是算计,是挣扎,是一分一厘的积攒,是一针一线的缝补。而穿越这沉重“骨”相的另一条“线”,或许就藏在这最平凡的专注、最质朴的情感,以及那枚来自洪荒的残片,与之产生的、微弱而神秘的共鸣之中。
窗外,不知谁家孩子偷偷点燃了一个鞭炮,“啪”的一声脆响,划破了年关凝滞的空气,也惊醒了沉思中的方唐。
年,真的要来了。无论贫富,无论甘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