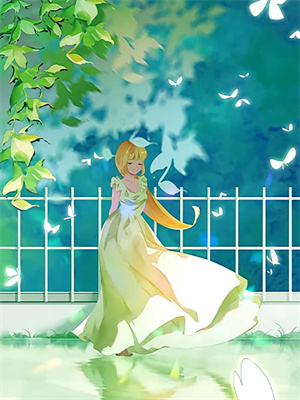简介
最近非常火的小说推荐小说琉璃烟火里讲述了林未晞沈砚舟之间一系列的故事,大神作者东山郎对内容描写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琉璃烟火里》以147317字连载状态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也喜欢这本书。
琉璃烟火里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梧桐巷的雨总在傍晚准时落下,淅淅沥沥打在 “时光匠造” 的木招牌上,把 “时光” 二字泡得发胀。林未晞正用抹布擦着柜台的玻璃,指尖划过积灰的柜角时,听见巷口传来拖沓的脚步声 —— 像是有人穿着不合脚的雨靴,踩在积水的青石板上,溅起的水花混着泥点,在暮色里画出模糊的弧线。
来人是个穿灰布短打的老汉,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的小腿上沾着草屑和泥浆。他怀里紧紧抱着个东西,用褪色的蓝布衫裹了好几层,怀里的轮廓方方正正,像是揣着块砖头。老汉站在铺子门口抖了抖伞上的水,竹骨伞 “咔嗒” 响了声,伞面的破洞漏下几滴雨,正好落在林未晞擦净的玻璃柜上。
“姑娘,收老东西不?” 老汉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乡音,牙床缺了颗门牙,说话时漏着风,“家里翻出个布包,看着有些年头了,或许能换几个钱。”
林未晞把他引进铺子,从墙角拖过张吱呀作响的木凳。煤炉上的水壶正冒热气,她倒了杯粗瓷茶碗递过去:“先暖暖身子,雨大,路上不好走吧?”
老汉接过茶碗时,手抖得厉害,茶汁溅在蓝布衫上,洇出深色的圆点。他这才慢慢掀开怀里的布衫,露出个红布包 —— 布面的红早已褪成浅粉,边角磨得发毛,针脚处还沾着些褐色的污迹,像是被水泡过又晒干的痕迹。红布包用细麻绳捆着,绳结打得紧实,解开时还得用指甲抠半天。
“就是这个。” 老汉把布包推到柜台上,布包落在绒布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前儿收拾老屋的梁上箱底翻出来的,我那死鬼婆娘说是她姥姥传下来的,放了快一辈子了。”
林未晞捏着布包的边角翻开,一股混合着霉味和樟木的气息扑面而来。红布里裹着的不是什么值钱物件,而是七枚铜钱,用棉线串在一起,线已经脆得一碰就断。铜钱滚落在绒布上,发出叮叮当当的轻响,像串被遗忘的风铃。
她捡起一枚放在掌心,铜钱边缘磨损得厉害,中间的方孔被磨得发亮,能照出模糊的指影。“乾隆通宝。” 林未晞用指尖捻着铜钱转了半圈,背面的满文已经看不清字迹,“普通流通币,存世量多,不值什么钱。”
老汉的脸一下子垮了,嘴角撇了撇,像是要哭出来:“那…… 那这包东西,连买袋米的钱都换不来?” 他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卷了支烟却没点燃,“我家孙子等着交学费,本指望这东西能凑个数……”
林未晞把七枚铜钱挨个摆开,借着煤炉昏黄的光仔细看。除了三枚乾隆通宝,还有两枚嘉庆通宝,边缘都带着磕碰的缺口,其中一枚的 “嘉” 字缺了最后一笔,像是被人用牙咬过。另外两枚是道光通宝,锈色很重,绿得发黑,用指甲刮一下,能掉下细碎的锈末。
“大爷您别急,” 她拿起最后一枚铜钱,这枚比其他几枚稍大些,颜色也更深,像是被火烤过的古铜,“这枚是康熙通宝,您看这字体,比别的浑厚些。”
铜钱正面的 “康熙通宝” 四个字笔画清晰,只是 “熙” 字左边多了一竖,成了个错字。林未晞忽然想起祖父的博古架上,曾摆过枚类似的错版铜钱,当时她觉得歪歪扭扭的不好看,祖父却笑着说:“错处也是记号,就像人脸上的痣,反倒成了辨识度。”
“错字的更不值钱吧?” 老汉叹了口气,把没点燃的烟卷重新塞回烟盒,“我就说嘛,哪有那么多值钱的老东西。” 他站起身要走,蓝布衫的后襟沾着片草叶,在煤炉的热气里轻轻晃。
林未晞把铜钱重新串好,正想包回红布里,指尖忽然触到康熙通宝背面的边缘 —— 那里有处极细微的凸起,不像是自然磨损的痕迹。她把铜钱凑到煤油灯前,灯光透过铜钱的方孔,在墙上投下个菱形的光斑,光斑里晃动着细小的尘埃。
“大爷您再等会儿。” 她从抽屉里翻出放大镜,镜片擦得锃亮,还是老钟表匠留下的。放大镜凑近铜钱背面,满文的 “宝” 字旁边,原本该是 “泉” 字的位置,却刻着个极少见的变体,笔画比常见的满文更曲折,像是条蜷着的小蛇。
林未晞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她记得《中国钱币史》里提过,康熙年间福建局曾铸造过一批特殊版别的铜钱,背面满文与其他局不同,因为铸量极少,市价一直很高。祖父的书房里有本《历代钱币图录》,其中一页就印着类似的铜钱,当时她只顾着看那页的茶渍,没仔细记细节。
“这枚您打算卖多少钱?” 她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指尖却因为用力,捏得放大镜的木柄微微发烫。
老汉愣了愣,搓着粗糙的手掌说:“你要是真心要,给…… 给五十块钱就行,够买袋米的。”
林未晞从帆布包里数出五张十元的纸币,递过去时,指尖碰到老汉的手。他的手掌布满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泥垢,接过钱时抖得更厉害了,把纸币小心翼翼折成小块,塞进贴身的口袋,像是揣着块滚烫的烙铁。
“谢谢姑娘,谢谢姑娘……” 老汉连连作揖,转身时撞在门框上,却没顾上揉疼的肩膀,踩着雨靴匆匆消失在巷口,竹骨伞在雨幕里晃成个模糊的黑点。
铺子突然安静下来,只有煤炉上的水壶还在咕嘟作响。林未晞把那枚康熙通宝放在掌心,用指腹轻轻摩挲背面的满文。放大镜下,那处特殊的刻痕越来越清晰,笔画间还残留着细小的铜锈,绿得像初春的青苔。
她翻出祖父留下的《历代钱币图录》,书页已经发黄发脆,翻动时得格外小心。书里夹着片干枯的玉兰花瓣,是从祖父书房窗外摘的,现在一碰就碎成了粉末。翻到福建局铜钱那页,图录上的拓片与手里的铜钱几乎一模一样,旁边标注着 “市价约合三个月房租”—— 正是她现在最需要的数目。
“哟,收着好东西了?” 陈叔端着碗热汤面站在门口,粗瓷碗里飘着葱花,香气混着煤炉的烟味涌进来,“我在隔壁就听见铜钱响,是哪个倒霉蛋把传家宝当破烂卖了?”
林未晞把康熙通宝递过去,陈叔用筷子夹着翻来覆去地看,面条的热气熏得他直眯眼:“这锈色是真的,包浆也厚,看着像窖藏过的。” 他忽然指着背面的满文,“这是福建局的?我前几年修过个福建商人的伞,他钱袋里就有枚类似的,说能换头水牛。”
煤炉上的水开了,林未晞灌了壶热水,水汽模糊了眼镜片。她把七枚铜钱小心放进红布包,红布的褪色纹路在灯光下像张网,网住了那些被时光遗忘的故事。忽然想起破产那天,父亲红着眼说 “以后再也不能给你买那些没用的老东西了”,现在才明白,真正的老东西从不是摆设,而是能在困顿时托底的底气。
傍晚收摊时,雨停了。梧桐巷的青石板上积着水,倒映着家家户户亮起的灯火,像撒了满地的星星。林未晞把红布包放进木匣子里,锁在柜台最下面的抽屉里。锁芯转动的 “咔嗒” 声,在寂静的巷子里格外清晰,像是给这段刚起步的日子,上了把安稳的锁。
她关铺子门时,看见老顾爷子拄着拐杖站在巷口,正对着天边的晚霞出神。老人转过身,看见她手里的木匣,忽然笑了:“丫头,老物件认主,就像雨认巷,到了该来的时候,自然会寻着路来。”
林未晞低头看了看掌心,那里还留着铜钱的凉意,像是块化不开的冰。她忽然想起祖父常说的 “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以前总觉得是故弄玄虚,现在握着那枚沉甸甸的康熙通宝,倒觉得这世上的相遇,原都是早有安排。
夜色漫进梧桐巷时,林未晞坐在煤油灯前,又拿出那枚康熙通宝。灯光透过铜钱的方孔,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像个跳动的问号。她不知道这枚铜钱会给她的生活带来什么,但指尖触到那处特殊的满文刻痕时,忽然觉得,从云端跌落的日子里,终于有了点能攥在手里的实在。
木匣子里的红布包轻轻动了动,像是里面的铜钱在互相碰撞。林未晞把木匣子放进床底,挨着那只还没修好的青花碗。黑暗中,她仿佛听见铜钱与瓷片的私语,在寂静的铺子里荡开涟漪,像是在说:别急,我们都在等你慢慢来。